
聖約翰座堂於一八四九年為崇拜開幕,而我們擁有的第一部鍵盤樂器很可能是在開幕後不久添置的塞拉菲娜風琴(Seraphine,其中一種簧風琴家族的實驗樂器)。於一八五四年,座堂添置另一部簧風琴將之取代。根據記錄,只於一八五三至五四年間,詩班員均是受薪的。但是,從那時起,詩班員則從未收個任何酬金。當時,在聖堂的南側耳堂曾為詩班搭建了一個長期使用的平台,以供詩班崇拜時用。
於一八五八年,座堂決定從英國購置一部管風琴,並於一八六〇年十二月送抵座堂。這部管風琴是由Bryceson and Son 建造,有三個鍵盤及二十五個音栓,共計一千一百二十四支音管。當然《音樂時報》(The Musical Times)更形容這部管風琴在當時「無疑是蘇彝士運河東面最好的一部」。不過,無情的氣候所導致的不穩定濕度令這部管風琴非常不可靠,維修費用亦非常昂貴。所以到一八八七年,一部由 J W Walker and Son 所建造的新管風琴,就在現時的聖米迦勒小堂的位置興建。
於一八六〇年,在奧斯雷爵士(Sir Frederick Ouseley)的推薦下,沈思特先生(Charles Frederick Augustus Sangster)成為聖約翰座堂首位風琴師及詩班長,達三十五年之久。儘管沈氏與當時的信託人(即管理座堂的平信徒)合作上出現問題,他仍大大提高了座堂及其他殖民地機構的音樂水平。現存的相片及信託人會議紀錄告訴我們早至當時,已經有女性詩班員負責詩班的高音聲部。
和德先生(Arthur Gordon Ward)於一八九五年接替沈氏,並於一九〇一年開始第一屆教區合唱節,其中包括哥爾(Alfred Robert Gaul)作曲的《聖城頌》(Holy City)。第三任風琴師及詩班長由福拿先生(Denman Fuller)繼任。在他的提議下,當時的Walker管風琴於一九一一年作了全面的徹底檢修。翌年,福氏為香港大學成立譜寫了一首聖頌。在一九一二年三月的香港大學開幕禮上,當時擁有三十人的座堂詩班為儀式獻唱。

梅臣先生(Frederick Mason)接替福氏成為座堂的第四任風琴師及詩班長。於一九二七年Blackett & Howden公司重修了管風琴,並將管風琴增建至有三個鍵盤及四十個音栓。每年國殤紀念日座堂詩班到和平紀念碑獻唱的傳統,亦在同時期建立。
黎爾福先生(Lindsay Lafford)於一九三五年接替梅氏,並留任至一九三九年。在立氏在任期間,女性詩班員以帽蒙頭的傳統終於被廢除,並可以穿着詩班袍。管風琴於一九三六年再次(亦很可能是日佔時期前最後一次)作全面檢修。專為合唱譜寫、教友不會參與的聖餐禮文樂章亦在當時引入,其中包括達克(Harold Darke)及史坦福爵士(SirCharles Villiers Stanford)的作品。
詩密夫先生(John Reginald Martin Smith)於一九三九年接替立氏,但於兩年後在赤柱的防衞戰事中喪生。 畢奇諾女士(Bee Bicheno)於戰後繼任,並逐步將詩班回復至戰前水準。
因舊有的管風琴復修費用十分昂貴,最後於一九四八年十月拆毀。從那時座堂便起用電子風琴。第一部電子風琴由Compton公司製造,共兩個鍵盤,於一九四九年開始使用。經過幾次替換後,於二〇〇一年座堂添置了一部Allen公司製造的四鍵盤電子風琴,共計七十個音栓。
於一九四九年,傅禮沙先生(Donald Fraser)接任成為風琴師及詩班長。他亦是當時教育司署的音樂指導,後來更成立了香港校際音樂節。當時的座堂詩班於每年聖誕期間,到何東爵士大宅邸及港督府獻唱聖誕歌。

郭鄭蘊檀女士於一九五四年接任傅氏,成為座堂風琴師及詩班長。當時,座堂詩班增至八十多位詩班員,並一度需要分為兩個詩班。郭太留任為座堂風琴師直至一九九一年,並由她的學生余必達先生繼任迄今。她繼續留任為榮休風琴師。於二〇〇九年,座堂以她的名義成立奬學基金,以協助具天分的青年人學習教會音樂。
符潤光先生於一九七九年接替成為詩班長。他當時是聖保羅書院的音樂科主任(直至二〇一三年榮休),讓座堂詩班可恆常地有年青的聲樂及器樂學生來參與。所以在詩班裏大部分的男性華人都畢業於(甚至仍然就讀)聖保羅書院。在符氏領導下,在座堂的節慶崇拜中開始引入以管弦樂伴奏的彌撒曲。詩班座位於一九六八年起改變了方向,轉向全部面向正堂。經過差不多半個世紀,詩班座位於二〇一一年回復到原本左右對坐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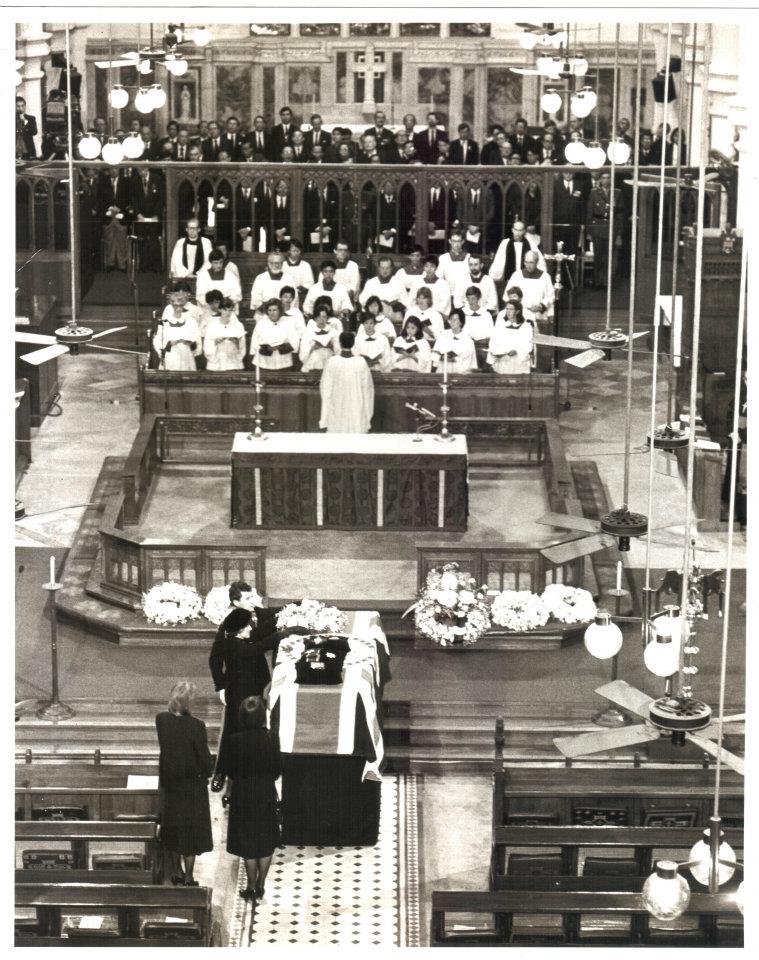
現在,座堂詩班大概有四十名詩班員,於每主日上午九時正的聖餐崇拜,及每月一次的頌唱早禱崇拜獻唱。詩班亦會在特別慶日,以及在婚禮或喪禮上獻唱。詩班獻唱的曲目與世界上一般座堂的音樂傳統大致相同。從文藝復興時期的複式音樂,到當代作曲家的特約作品皆有。座堂詩班之外,在座堂的大家庭中還有六個詩班,分別在普通話、菲律賓語、兒童及家庭崇拜、以及每月一次的頌唱晚禱崇拜中獻唱。